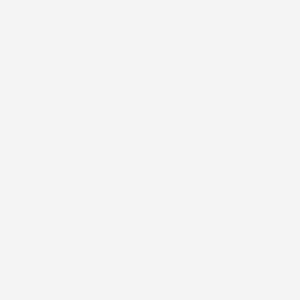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产品详情
- 产品参数
- 产品评论
◎名家集体点赞的巨人巨作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钟爱毛姆,《1984》作者乔治·奥威尔对毛姆讲故事的能力“无限钦佩”,《美国的悲剧》作者德莱塞称“《人生的枷锁》是天才的著作”,毛姆认为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不如《人生的枷锁》让他满意。本书有如此多、如此高的赞誉,毛姆迷们还不快快摆上案头?
◎毛姆写给在现实中迷茫的每一个人
你的命运,自己主宰。本书主人公菲利普本该是富二代,却天生跛足,自幼父母双亡;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讨厌他,同学嘲笑他,爱人背叛他……他学画不成,转而学医,却几乎因对他虚情假意的人荒废一生。紧要关头,菲利普摆脱了诱惑,主宰了命运,拥有了爱情,走进了幸福人生。
◎名家新修全译本
◆译者黄水乞教授,翻译家,科班出身,自1978年起便在厦门大学从事英语经贸教学与研究工作,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研修与生活,这保证了本版有着较高的翻译水准。
◆本版为新修订、无删节全译本。经过黄水乞先生全面修订,译文更准确,文字更精炼,表达更传神。而且本书由黄教授一人独立翻译,保证了译文风格、语言表达的统一。
◆对书中提到的西方传统文化及相关知识,如西方节日、传说、典故、神话人物、地名、人物等,逐一注解。
【内容简介】
《人生的枷锁》部分取材于毛姆早年的真实生活经历,由作者精心构思十数年创作而成,处处透着作者对人生、艺术、信仰的探讨,奠定了毛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
主人公菲利普出身于上层社会,却自幼父母双亡,而且先天跛足,在冷漠的寄居生活中度过了童年,又寄宿在满是虚伪氛围的皇家公学。步入社会后,他开始学习绘画,觉得自己没有天分后转而学医,却几乎为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荒废学业。饱尝世态炎凉、大彻大悟之后,他摆脱了情欲纠缠,放弃了周游世界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决定和一直照顾、疼爱自己的女子萨利一起生活。
这是一部小说版的励志书。通过菲利普之口,毛姆这样说:“我不考虑将来。要是我既要想着明天,又要操心今天,生活就没有意思了。每当事情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时,我总发现天无绝人之路”。
【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被誉为“天才的小说家”。
出身于律师家庭,但和笔下的菲利普一样,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抚养。上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辱,因此性格孤僻、敏感而内向。这些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曾在伦敦医学院学医,期间了解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学会了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因此作品不仅题材丰富,而且洞悉人性,对底层人民充满了人文关怀。代表作有《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和《面纱》等。
译者简介
黄水乞,翻译家,厦门大学国贸系教授。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1978年起在厦门大学从事英语经贸教学与研究,主要译作有《人生的枷锁》《呼啸山庄》《雾都孤儿》等,著有《学生英汉五用词典》《当代英汉双解分类用法词典》等。
【前言】
作者序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
对一个作家来说,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德叙述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普劳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劳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对不当之评论也易于被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就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如同其他小说一样,究竟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原稿校正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思的丽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索取一百磅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社。结果呢,哪怕我的索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此书的种种经历。我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只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萦绕了。它们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至于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为摆脱它们的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小说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出版界经理们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明了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剧院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艾赛亚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书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已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中的一本书名,称之为《人生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首次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的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至于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过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多·德莱塞给《新共和》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
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所经历的那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新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免费在线读】
拂晓,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阴冷的空气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女用人走进屋里,一个小孩正在里头酣睡。她拉开窗帘,机械地望了一眼对面的房子——一幢有门廊的灰泥房子,然后走到小孩床边。
“菲利普,醒醒。”她说。
她掀开被窝,把他抱起来,带他下楼。孩子依然睡眼惺忪。
“你母亲找你。”她说。
她打开楼下一个房间的门,把小孩带到一张床上,床上正躺着个妇人。她就是孩子的母亲。她伸开双臂,小孩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他没有问为什么被喊醒。妇人吻着他的眼睛,用一双瘦削、纤细的手隔着他那件白法兰绒睡衣抚摸着他温暖的身躯,将他搂得更紧了。
“宝宝,你还困吗?”她说。
她的声音很弱,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小孩没有回答,但惬意地笑了。在这又大又暖和的床上,还有柔软的双臂抱着他,他感到很高兴。他蜷着身子,紧贴着母亲,想把自己缩得更小一点,并且睡眼蒙眬地吻了她一下。不一会儿,他合上眼,又睡着了。大夫走过来,站在床边。
“哎,请先不要把他抱走。”她呻吟道。
医生严肃地看着她,没有答话。妇人知道孩子不允许在这儿久待,就又吻了他一下。她的手顺着他的身躯抚摸下来,一直摸到他的脚;她把他的右脚握在手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然后,又慢慢地把手伸到左脚上。她呜咽起来了。
“怎么啦?”大夫说,“你累啦。”
她摇摇头,说不出话来,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大夫俯下身子:“我来把他抱走。”
她太虚弱了,无力违拗大夫的意愿,只得让他抱走了。大夫将
他交给保姆:“你好把他放回他的床上去。”
“好的,先生。”
小男孩被抱走了,他还睡着。这时,孩子的母亲伤心地哽咽起
来。“他以后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想安慰她,但不久,由于她精疲力竭,哭声停止了。
大夫走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桌上躺着一个死产的婴儿,用
一条毛巾蒙着。他掀开毛巾看了看。大夫和妇人那张床中间隔着屏
风,但妇人猜出了他正在干什么。
“是女的还是男的?”她低声问护士。
“又是个男孩。”
妇人不再吭声了。过一会儿,保姆回来并走近病榻。
“菲利普少爷一直睡着。”她说。
一阵沉默,大夫又按了按病人的脉搏。
“眼下我用不着在这儿了,”他说,“早饭后我再来。”
“我送你出去,先生。”保姆说。
他们默默地下楼,到了门厅,大夫收住脚步。
“你已派人请凯里太太的大伯了,是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吗?”
“不知道,我正在等电报。”
“孩子怎么办?我想他好离开这儿。”
“沃特金小姐说要带他走,先生。”
“她是谁?”
“孩子的教母,先生。你看凯里太太还能好吗?”
大夫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