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详情
- 产品参数
- 产品评论
产品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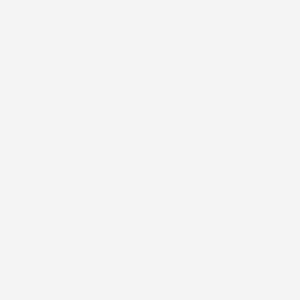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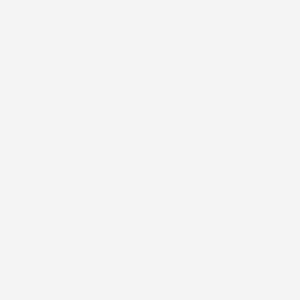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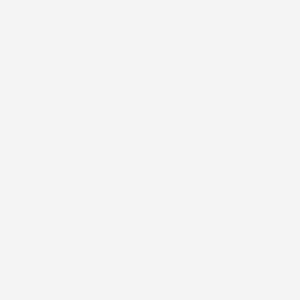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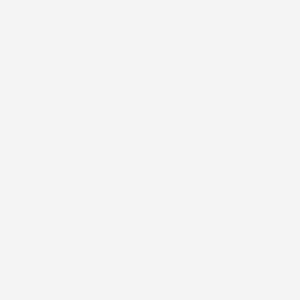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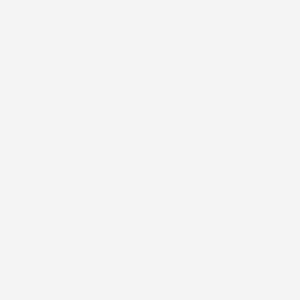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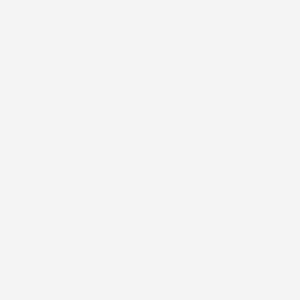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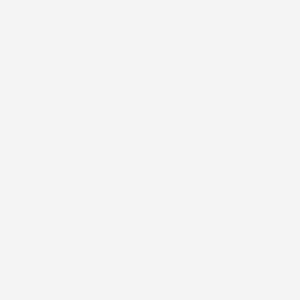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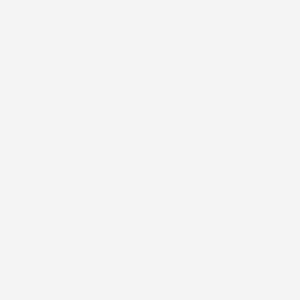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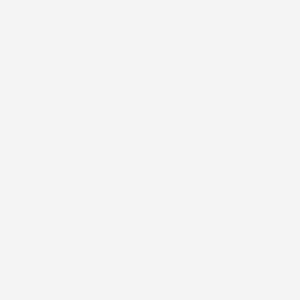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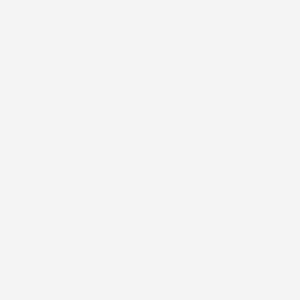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一句顶一万句》是**作家刘震云的扛鼎之作,也是刘震云迄今为止最成熟大气的作品,并在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分上下两个部分,前半部“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卖豆腐老杨的二儿子杨百顺百事不顺,他一生改了三次名:为了寻个营生,被天主教神父老詹纳为教徒,改名杨摩西;给县长种地时因为一个尿壶得罪了县长,提心吊胆中有人说媒,便倒插门嫁给馒头铺的吴香香,改名吴摩西;吴香香给吴摩西扣了顶绿帽子,吴摩西带着吴香香和前夫的女儿巧玲假意去寻与人私奔的妻子,路上又把巧玲丢了,失望之中,要离开故乡,从此用喊丧的罗长礼的名字度过余生;后半部“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巧玲被卖到陕西,成了曹青娥,嫁给牛家,儿子牛爱国也是假意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又想到自己从前的相好,想起母亲的老家,于是走回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作者简介
刘震云,汉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文字。
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
2018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精彩书评
国外媒体评论
刘震云的作品复杂繁绕,但每一笔都有寓意。于荒诞幽默的情节中,精准地描绘出各类人物的精神肖像。——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的时候,也会笑出声来。——美国《柯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
刘震云善于描写复杂的生活——他将各个社会阶层的纵横交错,描述得如此丰满和惊心动魄。 ——美国《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大家十分欣赏刘震云的小说,是因为他对事物之间的差异,体察得细致入微,这些差异又令人啼笑皆非。——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刘震云是结构主义大师,他用十分柴可夫斯基式的写法,揭示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背后,还有这么多深刻的联系。——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
刘震云用罕有的洞察力描写了生活这个巨大机器中的细小齿轮,游走于《愚比王》式的荒诞不经和卡夫卡式的魔幻寓言之间。——法国《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
刘震云是北京的卡夫卡。——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刘震云的文体是极简主义。他以大师手笔,成功地对不同生活阶层的色彩做了复杂、生动和通透的展示。——瑞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
刘震云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智利《信使报》El Mercurio
刘震云的小说智慧而幽默,一扫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阴暗、沉闷的固有印象。——日本《图书新闻》図書新聞
……
精彩书摘
四十多年前,老詹来延津传教时,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延津是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全县三十几万人,天天能吃饱饭的,仅有一万多人,延津人瘦,源头就在这里,吃饭吃个五成,就放下了筷子。主可怜见,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本欲修个小教堂,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能容百十来人。老詹虽不适合传教,但适合盖房子,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粗通建筑;砖瓦还是那些砖瓦,木料还是那些木料,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北两面,东、南两面改为土墙;屋顶背阴面用瓦,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木料不够,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解成板子;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教堂盖起来,能容三百来人。四十多年过去,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九天之内,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多年来,在延津基本空着。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要办“延津新学”,没有学堂,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有教义之争,不好告状,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但老詹并没有气馁,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杀猪者,传教者,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邦邦”地磕着烟袋:
“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
“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
“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
“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前言/序言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稗野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部。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